走进文物修复师,感受文物“活化”的力量
近日,秦陵铜车马博物馆基本陈列“青铜之冠——秦陵彩绘铜车马”获得了第十九届(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殊不知,该文物出土时破损严重,大部分车马碎片,受压变形,锈迹斑斑。在经历了整整8年的时间,于1980年出土的一组两乘车马终于重见天日。而这些文物能够还原完好地展现在每一位游客的眼前,少不了每一位文物修复工作者的付出。
文物修复师也被称做“文物医生”,他们是弥合历史隙罅的智者,更像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把文物从时间长河里“打捞”出来。经过他们的治愈,让文物“起死回生”,并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
1988年至1989年,文物修复师杨文宗参与了秦陵铜车马二号车的修复,并大获成功。30多年来,杨文宗承担了多项文物保护修复任务,保护修复过包括古代壁画、青铜、陶瓷、金银、砖石质在内的数千件(组)不同种类的文物,尤其是在古代壁画的保护修复方面,揭取、搬迁、修复和加固过的壁画共计数百平方米,涉及汉、北魏、唐、辽、金、宋等多个朝代。
“作为一名文物修复人员、一个专业的文物保护者,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多地把自己的技术传承给年轻人。”这是杨文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后辈的期望。
而同样从事文物修复30余年的还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许言。在许言眼里,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是每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修中国的文物和国外的文物,从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角度来说,没有先后排序。20多年来,到海外修复的世界遗产就是许言做出的最好注解。
许言参与的古迹修复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尼泊尔的九层神庙,乌兹别克斯坦的希瓦古城等。其中,在柬埔寨吴哥遗址的修复让他印象最为深刻。1992年吴哥古迹被列为濒危遗产,1993年柬埔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拯救吴哥古迹国际行动,中国派代表团参加首届吴哥古迹保护国际大会,明确表示参加拯救吴哥古迹国际行动。面对成千上万块散落的巨石,要将其重新“黏合”成一千多年前的样子,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无数个查阅资料、分析数据的夜晚,无数个指挥施工、现场测绘的白天,无数次的标号,无数遍的检测,才让古迹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许言认为,文物保护工作,是用人生几十年的短暂岁月,去接触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技术和文化。“我们不仅是在修复文物,更是在接续被打断的历史和文明脉络。通过跨越时空的对话驱动文明前行。”
文物修复还包括古籍和字画。18岁那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张艳与父母移居新加坡,随后入籍成为新加坡公民。过去30年左右,她一直从事书画修复师的工作。
张艳与79岁的父亲张孝宅是当地书画修复界的“金字招牌”。据了解,博物馆、私人藏家、拍卖行,都会将收藏的古字画送到这对父女档开设的“文保斋”进行修复。
经张孝宅之手修复的作品包括明代仇英、唐伯虎、董其昌、文征明,清代的任伯年、郑板桥、赵之谦、倪甜、王铎及近代的徐悲鸿、张大千等人的作品。
张艳10岁开始跟随家人学习熬煮修复画作所需用到的浆糊。掌握了熬浆糊后,她就开始学磨刀,慢慢熟悉修画的所有步骤与工具。古书画修复的步骤很多,最核心四个步骤是洗、揭、补、全。洗画即清理表面的尘埃或遗留在上面的污迹,做到“修旧如旧”;其次是揭命纸,即画芯背面的托纸;最后就是补洞和贴断纹,补全残缺褪色之处。
在张艳的修复生涯中,最难忘的还是与父亲一同修复的光绪皇帝御书。最初打开御书时,破损程度令人堪忧。装御书的铜筒长时间挂在牌匾上,御书单为画心,没有任何的装裱措施保护。修复期间,张艳陪伴父亲左右,二人一同拼画、全色、补绢,配合默契。在文物保管中心的修复室里,足足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才完成整体修复。
修画的过程是孤单且漫长的,但是张艳却从中找到了不一样的乐趣。张艳喜欢放些华乐伴奏,随着笙箫鼓瑟的旋律,进入画中情景。有时修得入神,仿佛与之产生了某种美妙的连结。张艳说:“很享受这种把旧物活化的过程。虽然画是没有生命的,但你把它修复完之后,就变成活的了,会有那种气韵生动的感觉。慢慢看会进入到画中的意境,了解创作的风格,其实是一种互动与对话。”
通过文物修复师的一双双巧匠之手,“生命垂危”的文物得以重生,其所承载的价值也由此能够世代相传。值得一提的是,以“博物馆文物‘活化’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主题的第17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将于6月1日至3日在广西北海举办。
届时,多位省级博物馆馆长以及文化领域相关的专家学者将围绕科技创新与文物的“活化”、数字化发展与博物馆的未来、文创产品的传统特色与现代审美议题,探讨数字化时代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传承的新趋势,展望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博物馆文物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的愿景,助推中国与东盟各国文化创意产业共同繁荣。
来源:联合早报、中国美术学院团委、央视网、开讲啦等
编辑:黄利霞
 第七届中国—东盟视听
第七届中国—东盟视听
 广西环保集团精彩亮相
广西环保集团精彩亮相
 东博智库|美国关税风
东博智库|美国关税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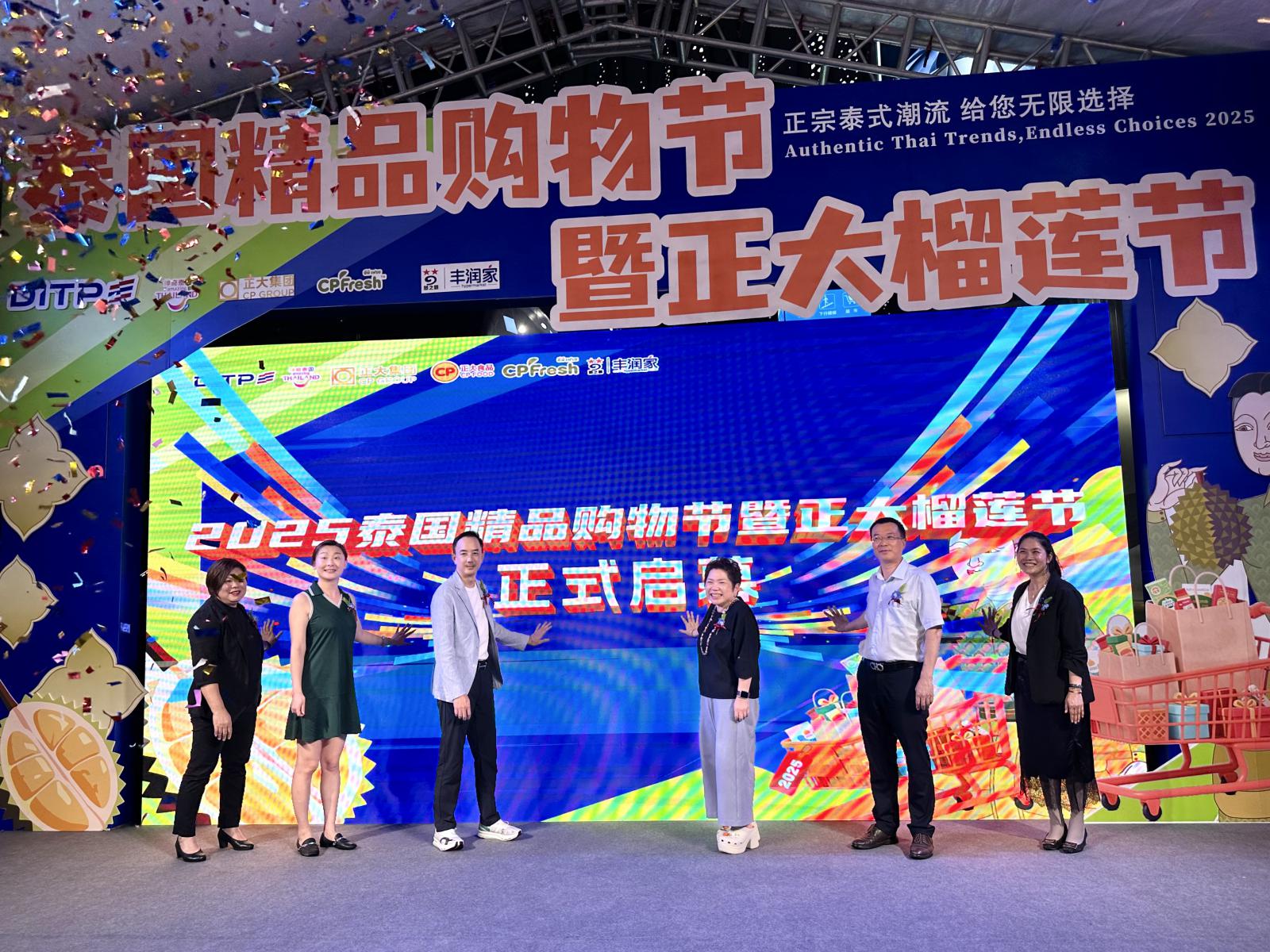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0186号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0186号